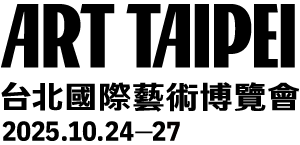凡德葛瑞夫帕斯卡
台灣,荷蘭
從自然到靈性:Pascal van der Graaf 與當代抽象的革新
本文由楊雅雯(北京大學博士)與chatgpt共同生成
摘要
Pascal van der Graaf(中文名楊文智,1978 年生於荷蘭)發展出一種獨特的藝術語言,連結了西方抽象與東方哲學。他早期紮根於自然的具象作品,逐漸轉向抽象,將畫布本身視為主體。透過不規則的畫布形制與摺疊表面,他把畫布轉化為能量的凝固體。在〈貝尼尼〉與〈香火袋〉等系列中,巴洛克的動態感與台灣文化的元素,使他的創作超越了純形式主義。他近期的〈綻放〉系列則運用神聖幾何與摺紙結構,將靈性力量具象化。
承續 Kandinsky、Mondrian 與 Malevich 的精神性抽象傳統,並呼應極簡主義與具體藝術的形式純粹,van der Graaf 引入褶痕作為呼吸、能量與身體動作的痕跡。他的作品超越了 Greenberg 所謂的「形式自主」,進入 Krauss 所稱的「擴張領域」,在繪畫與雕塑之間、文化與文化之間運作。
定居台灣後,van der Graaf 吸收了道家「順其自然」的思想,以及太極與氣功的修習。每一道摺痕既是一種修煉的行為,也是能量流動的視覺化,使繪畫轉化為身體、精神與形式的互動。他的作品同時是藝術家內在修行的痕跡,也是觀者的冥想對象,並批判性地追問藝術是否真的能夠傳遞靈性的力量。佔據 Homi Bhabha 所謂的「第三空間」,van der Graaf 的藝術既非全然荷蘭,也非純粹台灣,而是一種「跨文化的靈性抽象」語言。他延伸了幾何抽象與極簡主義,並注入能量與靈性共鳴,使他的創作在當代藝術中確立獨特位置——這種抽象不僅是形式上的革新,更是文化的綜合與哲學的探問。
楔子
Pascal van der Graaf(楊文智)的藝術歷程,標誌著近二十年不斷的探索與自我追問——一場從具象走向抽象的多階段旅程。2002 至 2020 年間,他不斷轉換主題與技法,從未停留在單一的語言裡,並一次次詢問自己:「我是這樣的畫家嗎?」他的答案始終是否定的。這段漫長過程不僅體現了實驗精神,也展現了他對西方與東方藝術傳統的深度對話。然而,真正的轉捩點並非他在 2007 年獲得荷蘭皇家現代繪畫獎,而是 2017 年移居台灣。經歷多年的探索與不確定後,他於 2022 年開始運用摺紙般的技巧折疊畫布,開啟抽象創作的新時代。透過「以影造影、以光作畫」,van der Graaf 建立了一種原創的跨文化靈性抽象語言,將疑惑與堅持轉化為更新與重生。
第一章:具象時期與自然的凝視
Pascal van der Graaf(楊文智)的創作生涯,若以藝術史的角度來檢視,其開端並非抽象,而是深植於自然的具象描繪。這一時期的作品,既延續了歐洲繪畫傳統中對自然的凝視,也逐漸揭示出他後來抽象實驗的核心母題——能量、流動與生成。從花卉系列到黑白繪畫,再到流動畫與海景風景,我們得以追蹤他如何在自然再現與形式純化之間,逐步走向屬於自己的抽象語言。
- 2002-2006花卉系列:自然生命力的凝視
早期作品中,花卉是 Pascal 最常描繪的主題。花卉作為繪畫題材,在西方藝術史上擁有悠久傳統:從 17 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靜物畫,到印象派對光影下花朵的再現,花卉一直是藝術家理解自然、表現生命力的載體。Pascal 的花卉並非簡單的自然再現,而更接近一種情感性的凝視。色彩鮮明、筆觸活潑,透露出藝術家對自然能量的敏銳感知。
在這些作品中,花朵既是主題,也是形式的實驗場。不同於傳統靜物畫的靜謐與克制,Pascal 的花卉畫作往往帶有動態感,彷彿在畫布上綻放、伸展。這種「生長性」的表現,後來在他對顏料流動的探索中被進一步強化,並最終轉化為對「能量」的抽象追求。
- 2006-2008黑白繪畫與鳥屋:形式純化的初現
2007 年,Pascal 以黑白畫作 For the bird 獲得了 荷蘭皇家藝術獎(Royal Award for Modern Painting)。這個獎項在荷蘭藝術界具有極高地位,專為年輕藝術家設立,旨在鼓勵他們的創新與實驗。對 Pascal 而言,這一獲獎不僅是職業生涯的重要里程碑,更是他藝術方向轉折的象徵。與花卉系列的鮮豔色彩相比,For the Bird 完全以黑白為主調。色彩的極端簡化,強化了結構與形態的重要性。作品的黑白對比,使觀者更直接地面對畫面的秩序與張力,而不再依賴色彩的誘惑。這種轉向,標誌著他逐漸放下對自然外觀的依附,轉而探索繪畫的純粹本質。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,這種純化的傾向與 20 世紀初抽象藝術的發展遙相呼應。Mondrian 在《新塑造的原則》中強調藝術應該擺脫具象再現,追求「純粹的塑造元素」。Pascal 的黑白繪畫雖仍帶有具象意涵,但其對結構的專注,已顯示出他與抽象傳統之間的潛在對話。
- 2009-2012流動畫:顏料的自生形態
在花卉與黑白之間,Pascal 發展出一系列「流動畫」作品。這些作品以顏料的自然流動作為創作的核心方法:顏料被傾倒、拖曳、讓其自由流淌,在偶然與必然之間形成形態。這一技法使得花卉與人物的形象不再由嚴格的輪廓界定,而是由顏料本身的運動生成。流動畫的重要性,在於它預示了 Pascal 對「自生性」的關注。作品不再是單純的再現,而是一種生成過程的痕跡。這種強調「過程」的態度,與 Jackson Pollock 的行動繪畫(Action Painting)有相似之處,但 Pascal 更關注的是顏料的「自然性」而非「身體性」。換言之,他不是用身體揮灑去征服畫布,而是讓顏料順應重力與材質的特性,自行找到形態。這種「隨物賦形」的觀念,與道家哲學不謀而合,並在他後來的折疊畫布中獲得更完整的實踐。
- 2012–2015:風景時期——腐朽、死亡與無常的隱喻
Pascal 轉向風景畫,特別是描繪破敗的舊磨坊場景,蘊含死亡與無常的隱喻。這一時期展現了他對失落與脆弱的探討,使其創作超越了形式實驗,進入存在論的提問。
- 2015–2020:海景——假期的輕盈與離去的渴望
Pascal 的風景與海景作品延續了荷蘭傳統對光線、空間與氛圍的關注,但又不同於敘事性的風景畫,而是強調能量場而非景物本身。波浪的起伏、風的力量、以及磨坊的腐朽,皆化為無常與死亡的隱喻,透過有節奏的筆觸與層疊的色彩加以呈現。隨著時間推進,焦點逐漸從外在的再現轉向內在的感受:自然不再只是景致,而是生命力流動的場域。在他後期的具象階段,海景畫中出現了船隻與休閒氛圍,表面看似輕快,卻暗含一股潛在的渴望——一種潛意識裡想要離去、尋找他方的欲望。他在 2016 年短暫停留澳門,並於 2017 年永久移居台灣,這些經歷進一步深化了這種感受。在這些後期作品中,流動的技法與海洋意象以及東方花卉圖像相融合,預示著他日後抽象創作中跨文化綜合的特徵。
小結
Pascal 的具象時期並非附屬,而是至關重要的出發點,鋪陳了他從自然再現走向形式純化的道路。花卉系列展現對生命力的凝視;黑白作品直面毀壞;流動畫顯示對生成的好奇;風景與海景則開啟了對腐朽與能量場的經驗探索。這五個階段,反映出一位藝術家始終不滿足,不斷探尋可能性,並追尋另一條道路。他的早期創作深深連結於傳統——無論是西方的技法與理論,或是東方的浮世繪與花卉意象——甚至他自己也形容那些作品是「大多受過去啟發」。然而,在這種重複之中,蘊藏了更新的種子。2007 年獲得皇家繪畫獎代表了肯定,但並非終點,而是對此前脈絡的匯聚,並未終結他的提問。最終,具象時期必須被視為基礎,為他日後抽象藝術的突破做好了準備。
第二章:轉折點的問題
現代畫家的歷史常強調某一個戲劇性的轉折點,但對 Pascal van der Graaf 而言,過程更為複雜。榮譽來得很早,真正的轉化卻在更晚之時。他的軌跡可以透過五個面向來釐清:
- 皇家獎:榮譽而非解答(2007)
憑藉《For the Bird》獲得荷蘭皇家現代繪畫獎,使 Pascal 贏得全國的關注與制度性的肯定。然而,這份榮耀並未消解他的藝術疑惑。評論家將該作視為邁向純化的一步,但對 Pascal 而言,它只是外在的里程碑,而非內在的轉化。
- 十年的實驗(2007–2017)
在獲獎之後,Pascal 探索了多種主題:流動畫、帶有腐朽隱喻的風景,以及既輕盈又不安的海景。每一階段最終都以不滿意收場。他不斷追問自己:「我是這樣的畫家嗎?」而重複出現的答案「不是」,驅使他在不同的表現方式之間不斷徘徊。
- 移居台灣(2017)
真正的轉折並非來自制度性的認可,而是生活的改變。移居台灣使 Pascal 沉浸於新的文化脈絡之中。與道家哲學的相遇、民間傳統的日常存在,以及太極與氣功的修習,為他帶來了關於流動、能量與精神的新觀念。這樣的環境動搖了他對西方傳統的依附,並開啟了更新的可能性。
- 身份的長期追問
2002 至 2020 年間,Pascal 的旅程是一場持續的自我追問。他常形容那段時期的作品是「大多受過去啟發」,呼應早期的大師與既有的語彙。他的不滿正源於此:他不願僅僅複製傳統,而是尋求一種根本不同的繪畫方式。
- 摺疊的突破(2022)
經過多年實驗與文化轉換後,Pascal 在摺疊畫布中找到新語言。在這裡,影子生成新的影子,光本身成為繪畫的媒介。這不僅是一種形式手法,更是二十年疑惑的解答。摺疊標誌著他長久追問最終凝結為肯定的實踐,使他得以超越傳統,進入跨文化靈性抽象的領域。
總結
總而言之,2007 年的皇家獎是一個里程碑,但真正的轉化卻發生在更晚期,透過移居、文化相遇與持續的自我追問。直到 2022 年,Pascal 才發現一種能回應他長期疑惑的形式,開啟了他成熟的摺疊抽象時期。
第三章:抽象歷程的開展 —— 形體的生成
如果說 2007 年的 Birdhouse 是 Pascal van der Graaf 的臨界點,那麼此後的十餘年間,他的創作徹底投入了抽象的疆域。他不再滿足於畫布平面的再現,而是開始探索畫布作為物質本身的可能性。這一歷程,從不規則畫布的嘗試,到橫摺與豎折的實驗,再到「貝尼尼系列」的雕塑性轉化,最後抵達「香火袋系列」與「綻放系列」的跨文化與靈性階段,逐步形成一個完整的抽象語言體系。
這一章節將梳理他抽象歷程的五個主要階段,並探討其在藝術史脈絡中的意義。
- 不規則畫布:突破矩形的束縛
Pascal 首先挑戰的,是繪畫最基本的載體——矩形畫布。在藝術史上,矩形畫布曾被 Clement Greenberg 視為繪畫自律性的保障:平面性必須依賴矩形邊界,才能維持繪畫的「純粹性」。然而,到了 1960 年代,Frank Stella、Ellsworth Kelly 等藝術家開始製作不規則形狀的畫布(shaped canvas),以此突破傳統。Pascal 的不規則畫布正延續了這一傳統。他嘗試將畫布裁切、拼接成各種非矩形的形態,使畫面本身不再是「窗口」或「再現場域」,而是物理性的對象。這一探索為他後來的折疊處理奠定了基礎:畫布不再是被動的載體,而是創作的主角。
- 橫摺與豎折系列:能量的凝固
在突破了畫布邊界之後,Pascal 將焦點轉向畫布表面。他開始在畫布上引入摺痕,形成橫向或縱向的折疊。這些摺痕不僅是形式的裝飾,更是能量的痕跡。從創作方法上看,摺痕並非隨意,而是經過藝術家身體力量的施加,將畫布壓折、固定,再以塗料覆蓋。每一道摺痕都記錄了身體的動作,猶如一次呼吸或一次太極動作的凝固。這讓畫布成為「能量的存檔」,不再只是平面的圖像。這一過程呼應了 Rosalind Krauss 的「擴延場域」理論:當繪畫不再只屬於平面,它就進入了雕塑與裝置的邊界。Pascal 的橫摺與豎折系列,正是這種跨界的實踐。
- 貝尼尼系列:巴洛克的再生
在豎折的基礎上,Pascal 發展出「貝尼尼系列」。靈感來自巴洛克雕塑家 Gian Lorenzo Bernini 的裙擺與布料雕刻,這些作品讓摺痕不再僅是幾何線條,而是具備柔軟流動的動態。這一系列的作品,呈現出一種「雕塑化的繪畫」。折痕像布料般下垂、翻轉,仿佛定格了運動的瞬間。這不僅是形式的進化,也是情感的延伸:巴洛克藝術追求的是戲劇性與感官性,Pascal 的摺痕則在冷峻的抽象中注入了感性的動勢。藝術史上,巴洛克與極簡主義常被視為對立:前者繁複華麗,後者冷峻克制。而 Pascal 的貝尼尼系列,正好將這兩者融合——在極簡的畫布上,展現出巴洛克的動態與戲劇感。這種跨時代的對話,使他的作品在抽象藝術的傳統中開啟新的路徑。
- 香火袋系列:跨文化的符號
移居台灣後,Pascal 開始吸收在地文化元素,最具代表性的便是「香火袋系列」。香火袋是台灣宗教文化中的護身符,常以摺疊布料或紙張製成,象徵祝福與庇護。Pascal 將這一文化符號引入創作,結合摺紙結構,將畫布折疊成類似香火袋的造型,再以烤漆上色。這些作品既有幾何的嚴謹,又帶有文化的溫度。它們不再是單純的形式實驗,而是承載了跨文化的意義:荷蘭的幾何抽象與台灣的宗教符號在此交織,形成獨特的語言。這一系列的出現,使 Pascal 的作品從「純形式抽象」跨越到「文化抽象」。它讓作品不僅在美學層面被閱讀,也在人類學與文化研究的脈絡中獲得新的解釋。
- 綻放系列(Blossom):神聖幾何的靈性實踐
最新的「綻放系列」是 Pascal 抽象歷程的集大成之作。這些作品以精密的摺紙結構為基礎,結合「神聖幾何」(Sacred Geometry)的圖形,如花形、六邊形、放射狀結構。在這裡,畫布不再僅是物質,而是能量的顯現。花朵的綻放象徵生命力的釋放,幾何的秩序則象徵宇宙的法則。作品成為一種「冥想物件」,邀請觀者進入沉思,感受內在能量的流動。這一系列呼應了 Hilma af Klint 的靈性抽象,也呼應了當代藝術家 Olafur Eliasson 對「感官經驗」的追求。然而,Pascal 的特殊性在於,他的靈性並非只在觀者體驗中,而是貫穿於創作過程:每一道摺痕都是他身體修煉的痕跡,每一個結構都承載著氣的運行。
- 學術定位:從形式到靈性的連續譜系
Pascal 的抽象歷程,從不規則畫布到綻放系列,構成了一條清晰的演進路徑:
- 不規則畫布:挑戰繪畫邊界。
- 橫摺與豎折:將能量凝固於畫布。
- 貝尼尼系列:融合極簡與巴洛克。
- 香火袋系列:跨文化的符號轉譯。
- 綻放系列:靈性幾何的終極實踐。
這一譜系顯示,Pascal 的作品並非斷裂式的風格轉換,而是一種連續的生成。從形式到文化,從能量到靈性,他逐步拓展抽象的邊界,使其不僅是視覺的實驗,更是精神的修煉。
小結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抽象歷程,是一場持續的形體生成。他通過畫布的變形與折疊,讓繪畫超越平面,成為能量的凝固體與文化的承載體。最終,他在「綻放系列」中將形式、文化與靈性融為一體,使作品成為「跨文化精神抽象」的典型。這一歷程不僅回應了抽象藝術的歷史傳統,也為其注入了東方哲思與當代靈性實踐,構成了他獨特的藝術史定位。
第四章:西方抽象的延續與革新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作品雖然植根於個人修煉與跨文化經驗,但若將其放入西方藝術史的框架來觀察,仍能清楚地看到他與抽象傳統之間的深刻關聯。他一方面承繼了抽象藝術的經典譜系:從 Kandinsky 的精神性、Mondrian 的幾何秩序,到 Malevich 的純粹形式,再到 Minimalism 與 Concrete Art 的冷峻克制。另一方面,他又突破了這些先行者所建立的邊界,將畫布推向雕塑性的物件,並融入身體能量與東方哲思,使其成為一種革新的抽象語言。
- 精神性抽象的延續
在 20 世紀初,Kandinsky 在《藝術中的精神性》一書中提出,抽象藝術並非形式的隨機組合,而是藝術家內在精神狀態的必然表達。他認為色彩、線條與形態能直接觸動觀者的靈魂。Mondrian 進一步在《新塑造的原則》中指出,藝術應當捨棄具象,再現宇宙的普遍秩序。Malevich 的「至上主義」更是將繪畫簡化為純粹的幾何形態,將正方形視為宇宙秩序的象徵。Pascal 的抽象探索顯然與這些先驅者同屬一個精神性傳統。他的折痕、摺紙結構和幾何圖形,並非僅僅是形式的裝飾,而是能量與精神的符號。與 Mondrian 不同的是,Pascal 的幾何不是理性的規劃,而是身體能量與自然流動的結果;與 Malevich 不同的是,他並未追求純粹的「零度形式」,而是讓形式與生命力結合。可以說,他延續了抽象的精神性使命,但將其轉化為更具身體性與能量感的表達。
- Minimalism 與 Concrete Art 的對照
1960 年代的 Minimalism(極簡主義)與 Concrete Art(具體藝術)強調藝術應當回到最基本的形態與材料。Donald Judd 提倡「具體對象」(specific objects),拒絕再現與隱喻;Ellsworth Kelly 透過單色形狀探索純粹的視覺效果;荷蘭的 Nul groep 與 Jan Schoonhoven 則以冷峻的幾何結構呈現秩序與重複性。Pascal 的作品與這些傳統有明顯的親緣關係。他的折疊畫布與豎折系列,延續了 Concrete Art 的秩序感與 Minimalism 的物件性。然而,他並不滿足於「冷峻」的形式,而是在摺痕中注入身體的力量與呼吸。這一點使他的作品與極簡形成對比:極簡追求「無我」,而 Pascal 的摺痕則是「有我」的能量痕跡。這種差異,使他的抽象更接近一種「精神極簡」或「能量極簡」,既保有形式的純粹,又不失內在的張力。
- Greenberg 的形式自律與其突破
Clement Greenberg 是現代主義藝術理論的核心人物,他在〈現代主義繪畫〉中主張繪畫應回到自身的本質——平面性、色彩與構圖。這一理論奠定了抽象繪畫的正統地位,但也導致了對「形式自律」的過度強調。Pascal 的作品可以說既承繼了 Greenberg 的觀念,又對其提出挑戰。他的摺痕與折疊,確實是對繪畫本質的反思:當畫布成為三維物件時,它仍然是繪畫嗎?然而,與 Greenberg 的「形式自律」不同,Pascal 的作品並不拒絕跨界,反而擁抱雕塑性與文化符號。他的香火袋系列便是明證:它既是抽象形態,也是文化符號的轉譯。這種跨界,使他超越了 Greenberg 的框架,走向 Krauss 所謂的「擴延場域」。
- Krauss 與擴延場域
Rosalind Krauss 在〈雕塑的擴延場域〉中指出,當代藝術不再受限於傳統媒介的分類,而是在雕塑、建築、景觀之間遊走。Pascal 的折疊畫布正好印證了這一理論。他的作品介於繪畫與雕塑之間:它有畫布的材質與顏料,也有雕塑的形態與體積感。這種跨界性質,使他的作品不再只是「繪畫」,而是「生成中的對象」。在此意義上,Pascal 的抽象是一種「擴延抽象」。它不僅延續了幾何抽象的形式語言,也擴展到雕塑、裝置與文化符號的領域。這種跨越,使他的作品能夠在當代藝術的多元場域中獲得新的解讀。
- 與當代荷蘭藝術的比較
在荷蘭當代藝術的脈絡中,Pascal 的作品也顯示出獨特性。與 Jan Maarten Voskuil 的「變形畫布」相比,Pascal 的折痕更強調能量與靈性,而非純粹的形式操作。與 Lieven Hendriks 等藝術家對幻覺與錯覺的探索相比,Pascal 的重點不在於視覺的欺騙,而在於精神的觸動。這種差異,使他在荷蘭當代藝術界佔有一個獨特的位置:既延續傳統,又開創新路。
- 學術定位:革新中的延續
總結而言,Pascal van der Graaf 的作品與西方抽象傳統密不可分。他延續了 Kandinsky、Mondrian 與 Malevich 的精神性使命,吸收了 Minimalism 與 Concrete Art 的形式純粹,也呼應了 Greenberg 與 Krauss 的理論框架。然而,他並未停留於延續,而是在跨界與跨文化的實踐中開啟革新。他的抽象不僅是形式的遊戲,而是能量、身體與靈性的綜合表現。因此,在西方藝術史的脈絡中,Pascal 的定位可被視為一種「革新的延續」:既紮根於抽象傳統,又超越其限制,將抽象帶入更廣闊的精神與文化場域。
小結
Pascal 的抽象創作不僅是對西方傳統的繼承,更是對其革新的回應。他把抽象從「形式的自律」推向「精神的跨界」,把畫布從平面轉化為能量場,並在荷蘭—台灣的跨文化經驗中,賦予抽象新的生命。這種延續與革新的雙重性,正是他在當代藝術史中最值得關注的特徵。
第五章:東方哲學與身體實踐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創作之所以在當代抽象藝術場域中具有獨特性,不僅因為他延續了西方抽象傳統,更因為他在作品中深度導入了東方哲學與身體實踐。自移居台灣後,Pascal 長期修習太極與氣功,並在創作過程中內化了這些身心訓練的經驗。這使他的作品不再僅僅是形式實驗,而是能量修煉的痕跡。
在這一章,我將從道家思想、身體修煉、折痕的意涵,以及跨文化的轉譯四個層面,探討 Pascal 如何將東方哲學引入其抽象語言。
- 道家思想:隨物賦形
道家哲學的核心,在於「道法自然」與「無為而治」。這種思想強調形態並非人為強加,而是源於事物內在的自生規律。Zhuangzi 在《逍遙遊》中提出「隨物賦形」,意指一切形態都應隨著自然的流動而生成,而非刻意雕琢。Pascal 的作品與此觀念高度契合。無論是橫摺與豎摺,還是綻放系列的摺紙結構,都不是預設的數學運算,而是讓畫布在摺疊與顏料流動的過程中自行找到形態。藝術家所做的,只是引導與順應,而非強制與控制。這一點與西方幾何抽象形成鮮明對比。Mondrian 透過嚴格的水平與垂直線條,建構出一種理性的秩序;Pascal 則透過折痕的自然生成,展現道家所謂的「自然而然」。兩者同樣追求秩序,但一個來自理性規劃,另一個則來自自然流動。
- 身體修煉:氣與能量的流動
Pascal 長期修習太極與氣功,這些身體實踐使他對「氣」的運行有深刻的體驗。在太極的語境中,氣是一種無形卻可感的能量,它隨呼吸與動作在身體與宇宙之間流動。在創作中,Pascal 將這種能量經驗轉化為物質痕跡。每一次折疊畫布的動作,都像是一個太極姿勢的凝固;每一道摺痕,都像是呼吸的瞬間被定格。觀者看到的不只是幾何形態,而是能量流動的殘影。這種方法,讓作品不僅是視覺對象,更是「能量的載體」。正如太極強調「以柔克剛」、「四兩撥千斤」,Pascal 的作品雖然以堅硬的畫布與烤漆為材質,卻在摺痕中展現出柔和的力量與韌性。這種剛柔並濟的特質,正是東方身體哲學與西方物質語言的結合。
- 折痕的意涵:呼吸的痕跡
折痕是 Pascal 創作中最具標誌性的語言。從藝術史的角度,折痕常被視為形式操作的結果;但在 Pascal 的語境中,折痕更是一種「呼吸的痕跡」。每一道折痕都不是隨機的,而是藝術家在身體與畫布互動過程中留下的力量軌跡。這種痕跡並不隱喻任何外部形象,而是直接呈現能量的存在。換言之,折痕是一種「能量的可視化」。在此,我們可以聯想到法國哲學家德勒茲(Gilles Deleuze)在《折疊:萊布尼茲與巴洛克》中對「折疊」的闡釋:折疊不是單純的形態,而是一種無限延展的動態。Pascal 的折痕與德勒茲的觀點不謀而合:它不是靜態的裝飾,而是能量在畫布中的流動與延展。
- 跨文化的轉譯:從荷蘭到台灣
Pascal 的作品之所以獨特,還在於它同時承繼荷蘭抽象的幾何傳統,並吸收台灣在地文化的元素。例如「香火袋系列」便是典型案例。香火袋作為台灣民間信仰的護身符,本身具有靈性與庇護的意涵。當 Pascal 將這一文化符號轉化為折疊畫布時,作品不僅是形式的實驗,也是文化意義的承載。這種跨文化的轉譯,使他的作品同時處於兩個語境之中:在荷蘭,它被視為抽象藝術的延續;在台灣,它則被閱讀為對在地文化的回應。這種雙重語境,使他在當代藝術的國際場域中具備特殊的定位。
- 學術定位:身體—能量—形式
綜合以上,我們可以將 Pascal 的東方哲學與身體實踐歸納為一個三重關係:
- 身體:太極與氣功的訓練,使他能以身體力量介入創作。
- 能量:摺痕與流動的形態,是氣運行的痕跡。
- 形式:這些痕跡最終凝固為幾何結構,進入抽象藝術的脈絡。
這三者的交織,使 Pascal 的作品不僅僅是形式的實驗,而是能量與精神的體現。這種「身體—能量—形式」的架構,使他在抽象藝術的語境中開闢出一條新路徑:從東方哲學出發,革新西方抽象的形式語言。
小結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在當代抽象藝術中脫穎而出,關鍵在於他將東方哲學與身體實踐引入其中。道家的「隨物賦形」讓他的作品具備自然生成的特質;太極與氣功的修煉,讓折痕成為呼吸與力量的痕跡;跨文化的轉譯,則使作品在荷蘭與台灣之間找到雙重定位。最終,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種「跨文化精神抽象」:既延續西方抽象的傳統,又融入東方的能量觀與身體哲學,構成當代藝術中少見的獨特語言。
第六章:靈性藝術的傳承與挑戰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作品,不僅僅是抽象語言的探索,更是靈性實踐的延伸。從花卉與流動畫的自然凝視,到折痕與摺紙結構的能量凝固,再到「綻放系列」的神聖幾何,他的作品始終指向一個核心問題:藝術是否能夠成為靈性力量的載體?這一問題使他的創作不僅與西方抽象藝術的形式傳統對話,也與「靈性藝術」的歷史譜系緊密相連。同時,他也清楚地意識到,藝術與靈性之間存在不可化約的張力:藝術可以指涉靈性,但能否真正傳遞靈性力量,卻始終懸而未決。
- 靈性抽象的歷史傳統
在 20 世紀初,Hilma af Klint 以其神祕主義的繪畫實踐,開啟了靈性抽象的序幕。她的作品大量使用幾何圖形、花卉符號與對稱結構,試圖將不可見的靈性世界具象化。Kandinsky 亦在《藝術中的精神性》中指出,抽象繪畫是表達「內在必然性」的方式,它能夠直接觸動觀者的靈魂。Mondrian 則進一步將抽象視為宇宙秩序的映照,透過水平與垂直線條建立精神秩序。這些先驅者共同奠定了「抽象作為靈性載體」的傳統。Pascal 的創作,無疑延續了這一傳統。他的折痕、摺紙結構與神聖幾何,都是將不可見的能量轉化為可視形式的嘗試。
- 當代靈性藝術的語境
進入當代,靈性藝術的形態更加多樣。James Turrell 透過光與空間,營造出接近宗教體驗的冥想環境;Olafur Eliasson 以光、水與鏡面,讓觀者感受自然力量的沉浸;Bill Viola 的錄像作品則以慢動作與宗教隱喻,探討生命與死亡的精神層面。Pascal 與這些藝術家同樣關注靈性經驗,但不同之處在於,他不僅強調觀者的感受,更強調創作者本人的修煉。對他而言,作品不是單純的「靈性氛圍營造」,而是修煉過程的痕跡。這使他的作品同時具備兩層靈性意涵:
- 創作過程的靈性:折痕與摺紙結構,是藝術家呼吸、力量與氣運行的凝固。
- 觀者經驗的靈性:幾何與色彩的結構,邀請觀者進入冥想狀態。
換言之,他的作品是一種「雙向靈性」:既是藝術家的修煉,也為觀者提供靈性體驗。
- 神聖幾何的當代表述
在最新的「綻放系列」中,Pascal 大量使用神聖幾何圖形(Sacred Geometry),如花形、放射狀、六邊形結構。神聖幾何自古以來被視為宇宙秩序的象徵,廣泛存在於宗教建築、曼陀羅與自然結構之中。Pascal 將神聖幾何結合精密摺紙技術,使作品同時具備嚴謹的秩序與自然的生長性。花朵的綻放,不僅是生命力的隱喻,也是能量釋放的象徵。在這些作品中,形式與靈性緊密結合,作品本身成為一種「冥想物件」,邀請觀者透過凝視進入內在沉思。這種做法,使他的作品在當代抽象藝術中佔有特殊位置:它既延續了 Hilma af Klint 的靈性抽象傳統,又回應了當代觀念藝術中對能量與感官的關注。
- 張力與質疑:靈性是否可被傳遞?
然而,Pascal 的作品並非一味地歌頌靈性。他同時懷抱著一種批判性的自覺:藝術是否真的能夠傳遞靈性力量?在創作過程中,他體驗到能量的流動與呼吸的痕跡,但當這些痕跡轉化為物質作品時,它們是否仍然保有靈性?觀者在觀看作品時,所感受到的力量,究竟是藝術家修煉的延續,還是單純的形式效果?這種質疑,使他的作品帶有一種哲學性的張力。它們既是靈性的實踐,也是對靈性可能性的懷疑。正如藝術史學者 Hal Foster 在《反美學》中所指出的,當代藝術的價值往往在於「揭露矛盾」,而非提供答案。Pascal 的作品,正是在揭露「藝術與靈性之間的矛盾」中,展現了其深度。
- 學術定位:靈性抽象的當代表徵
綜合而言,Pascal 的作品可被定位為「靈性抽象」的當代表徵:
- 他延續了 20 世紀初的靈性抽象傳統(Hilma af Klint、Kandinsky、Mondrian)。
- 他呼應了當代靈性藝術的語境(Turrell、Eliasson、Viola)。
- 他在創作過程中實踐修煉,使作品成為能量痕跡。
- 他懷抱批判性,質疑藝術能否真正承載靈性力量。
這種雙重性,使他的作品在當代藝術中顯得獨特:它既是肯定的,也是懷疑的;既是靈性的實踐,也是哲學的提問。
小結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作品,將抽象藝術推向靈性層次,同時揭示藝術與靈性之間的張力。他既延續了靈性抽象的傳統,又在當代語境中賦予其新的意義。最重要的是,他的作品並非停留於形式,而是源於身體修煉與能量經驗,使其成為「跨文化精神抽象」的重要代表。
第七章:跨文化精神抽象的定位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作品,最終不僅僅是抽象的形式實驗,也不只是靈性的藝術實踐,而是處於「跨文化精神抽象」的場域之中。這一定位,來自他個人生命經歷(荷蘭成長、台灣定居)、文化吸收(歐洲抽象傳統、東方哲學與在地信仰),以及他在藝術史傳統與當代語境間所建立的對話。
- 荷蘭的抽象傳統
荷蘭在現代藝術史中,始終是幾何抽象的重要發源地之一。從 Mondrian 的新造型主義(De Stijl),到 Nul groep 與 Jan Schoonhoven 的極簡幾何,再到當代的 Jan Maarten Voskuil 的變形畫布,荷蘭藝術家一再挑戰繪畫的邊界。Pascal 的創作與這一傳統緊密相關。他的折疊畫布與摺紙結構,繼承了荷蘭抽象對形式純粹化的追求,同時推進到新的領域:幾何不再是冷峻的結構,而是帶有能量與靈性的生成物。換言之,他既是荷蘭抽象的繼承者,也是革新者。
- 台灣的文化吸收
自 2016 年定居台灣以來,Pascal 將在地文化元素引入創作,最具代表性的便是「香火袋系列」。香火袋作為民間信仰的護身符,承載庇護與祝福的象徵。Pascal 將其結構轉化為摺紙畫布,既保留了幾何的嚴謹,又融入了宗教的溫度。
這種轉化,不是簡單的文化挪用,而是一種內化。Pascal 並非外部觀察者,而是親身參與台灣的生活,將在地文化視為生命經驗的一部分。這使得他的作品在國際場域中,能夠同時被閱讀為「荷蘭抽象」與「台灣文化」的交會。
- 個人修煉與跨文化身分
Pascal 的作品之所以具有精神性,不僅來自於形式與文化,更來自於他的個人修煉。他長期練習太極與氣功,並將這些身體經驗轉化為創作方法。每一道折痕都是呼吸與力量的痕跡,每一個結構都承載氣的運行。這種修煉,使他的作品不僅是藝術形式的創新,更是一種精神實踐。作為一位在荷蘭成長、在台灣生活的藝術家,他的身分本身就是跨文化的。這種跨文化身分,使他的作品成為不同文化力量交會的場所。
- 國際語境中的定位
在當代國際藝術場域中,Pascal 的作品既可與西方抽象對話,也能在亞洲的文化脈絡中被理解。這種「雙重可讀性」正是跨文化藝術的特徵。在歐洲,他的作品可被視為對幾何抽象與極簡主義的延續與革新;在亞洲,則可被解讀為對道家哲學與宗教文化的當代詮釋。這種雙重語境,使他的作品不僅具有地方性,也具備國際性。這裡,我們可以借用 Homi Bhabha 的「文化混雜性」(cultural hybridity)概念。Bhabha 指出,後殖民語境中的文化不再是單一的,而是在不同文化交會處形成「第三空間」。Pascal 的作品正處於這樣的「第三空間」:既不是純粹的荷蘭抽象,也不是單純的台灣文化,而是兩者交會後生成的新語言。
- 跨文化精神抽象的學術定位
綜合而言,Pascal 的作品可被定位為「跨文化精神抽象」:
- 跨文化:在荷蘭抽象與台灣文化之間,在西方理性與東方靈性之間,形成混雜的語言。
- 精神性:透過太極、氣功與神聖幾何,使作品成為能量與修煉的痕跡。
- 抽象性:以折疊與摺紙結構,將畫布推向幾何與雕塑的邊界。
這三個層面的交織,使 Pascal 的作品不僅延續了抽象藝術的傳統,也為其開啟了新的方向:抽象不再只是形式的純粹化,而是文化、身體與精神的綜合實踐。
小結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作品,在國際藝術史的語境中,可以被定位為「跨文化精神抽象」的代表。他既繼承了荷蘭抽象的傳統,又內化了台灣的文化元素;既實踐了個人的身體修煉,又展現了全球語境中的文化混雜性。最終,他的作品不僅是形式的遊戲,更是精神的載體與文化的交會點。
結論:Pascal van der Graaf 的藝術史定位
回顧 Pascal van der Graaf 的創作歷程,可以清楚看到一條從具象走向抽象、從自然凝視走向精神修煉的路徑。這條路徑並非斷裂式的,而是一種漸進的生成:它既有內在邏輯,也與外在的藝術史傳統、文化環境相互呼應。
- 從自然到形式
在早期,Pascal 的創作深受自然啟發。他以花卉、風景、流動畫為主題,透過色彩與筆觸表現生命力與能量流動。這一階段的作品,不僅延續了荷蘭風景畫的傳統,也透露出他對「自然力量」的關注。2007 年的 Birdhouse,則將這一探索推向純化的極致:黑白對比取代了鮮豔色彩,結構性壓過了自然再現。這一轉折,使他進入抽象的門檻。
- 折疊畫布與抽象的生成
自 2007 年後,Pascal 的重心轉向畫布本身。他透過不規則畫布、橫摺與豎摺,讓畫布成為能量的凝固體。進入「貝尼尼系列」後,折痕不僅是幾何,更帶有巴洛克式的動態。再到「香火袋系列」,他將台灣文化引入抽象,使作品不再只是形式遊戲,而是文化與精神的交會。最新的「綻放系列」,則以神聖幾何與摺紙結構,展現靈性力量的可視化。這一抽象歷程,體現了從形式到靈性的演進。
- 西方抽象的延續與革新
Pascal 的作品延續了 Kandinsky、Mondrian、Malevich 所奠定的精神性抽象傳統,也呼應了 Minimalism 與 Concrete Art 的形式純粹。但他並未停留於形式自律,而是將折痕與能量結合,使抽象具有身體性與靈性。他突破了 Greenberg 的「形式自律」框架,走向 Krauss 所謂的「擴延場域」——介於繪畫與雕塑之間,並進入跨文化的維度。
- 東方哲學與身體修煉
Pascal 在台灣的生活,使他吸收了道家「隨物賦形」的思想與太極、氣功的身體經驗。每一道折痕,都是呼吸與力量的痕跡,是能量流動的可視化。他不再追求理性的幾何,而是讓形態自然生成。這種創作方式,既是形式的革新,也是修煉的延伸。作品因此成為「身體—能量—形式」的交織體。
- 靈性藝術的承繼與質疑
在靈性藝術的脈絡中,Pascal 延續了 Hilma af Klint 與 Mondrian 的傳統,也與當代的 James Turrell、Olafur Eliasson 形成對話。但他的特殊性在於,他不僅在觀者經驗中營造靈性氛圍,更在創作過程中實踐修煉。他的作品因此同時具備「藝術家修煉的痕跡」與「觀者冥想的物件」兩重屬性。然而,他也保有批判性:藝術是否真的能傳遞靈性力量?這種質疑,使他的作品不僅是肯定靈性的工具,也是哲學性的提問。它們揭露了藝術與靈性之間的矛盾,讓作品更具深度。
- 跨文化精神抽象的定位
Pascal 的獨特之處,在於他處於「跨文化」的位置。荷蘭抽象的幾何傳統,與台灣文化的符號與哲思,在他的作品中交會。這種文化混雜性,使他的作品既能在西方抽象的譜系中被理解,也能在亞洲文化的語境中被閱讀。他的作品正處於 Homi Bhabha 所謂的「第三空間」:既不是純粹的荷蘭,也不是單一的台灣,而是交會後生成的新語言。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藝術史定位,可以歸納為「跨文化精神抽象」:
- 抽象性:他延續並革新了幾何抽象與極簡主義。
- 精神性:他將太極、氣功與神聖幾何引入作品,使其成為能量與修煉的痕跡。
- 跨文化:他在荷蘭與台灣之間,形成雙重語境與文化混雜性。
這三重特質,使他在當代藝術中佔有獨特位置。他的作品不僅延續了抽象藝術的傳統,也拓展了其疆域,將抽象轉化為文化與靈性的綜合實踐。
Pascal van der Graaf 的作品,是一種「生成中的抽象」:它既來自自然的凝視,也來自身體的修煉;既延續了西方藝術史的抽象傳統,也吸收了東方哲學的能量觀;既是形式的革新,也是靈性的探問。最終,他的作品在當代藝術中建立了一種新的位置:跨文化精神抽象的代表。